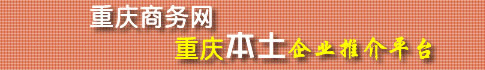重现民国时期的重庆老街。

仿佛回到老重庆。

工人在进行修缮。记者 杨新宇 实习生 胡逸鸣 摄
“号外!号外!”一声声吆喝,瞬间将人拉回战时陪都:报童满街奔跑、滑竿上上下下、老茶馆人声鼎沸。
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,那些吆喝声已渐行渐远。找寻遗失的民俗,就是触摸历史的脉络。两江国际影视城沿历史的刻度回溯,努力再现老重庆、陪都时期的民风民俗。
茶馆:旧重庆的重要社交场所
“1938年,重庆的茶馆达2950个。”两江国际影视城管理单位负责人谢波说。如今,在两江国际影视城内,就复原了五六家老重庆茶馆。这些茶馆曾在陪都时期名声远扬,生意红火。
老重庆茶馆分成几大类,分别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:高档茶馆,专门招待达官贵人;帮会茶馆,旧社会袍哥们谈公事的地方;低档一点的,则是贩夫走卒们聚会的地方。茶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,是各种信息交流的重要地方。
如今复原的老茶馆内,木桌、长条凳、盖碗茶一样不少,门口有知客领客,幺师穿堂而过。搀水也很讲究,三起三落,“头道发、二道冲、三道泡”的规矩不得马虎。
走进影视城坐一坐老茶馆,能体验到原汁原味的老重庆。
黄包车:坐一盘出行特别有面子
坐完茶馆出门,一辆黄包车正好停在马路旁。抬脚迈进黄包车,招呼车夫要去的地址,车夫把车一抬,便开始一路小跑。
根据相关资料显示,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黄包车的车费不菲,法定力资起价是铜板1000文,每加一段多交800文,从两路口到较场口,全程算下来要5000文。
1929年,重庆城区第一条马路竣工,自七星岗起,经观音岩、两路口、上清寺至曾家岩。同年,黄包车出现在这条马路上。据《重庆交通志》记载,最早这批黄包车共18辆,由于车轮用橡胶制作,坐着很舒服,在多坡多巷、道路狭窄的重庆城行驶起来相当便捷,很快获得了市民的认可。到1940年,全市登记在册的黄包车有2019辆。
重庆山高路不平,拉车十分考验技巧,上坡要一鼓作气,遇有长下坡,车夫便吊在车把上,蜻蜓点水般跳跃下滑,不但车夫危险,乘客都捏一把汗。梁实秋曾在其文章中形容过在重庆坐黄包车的感觉:“连大气也不敢喘,岂止胆战心惊。”
报童:重现抗战时新闻大战
“号外!号外!“在很多抗战题材的影视剧里,经常都会出现这样的吆喝声,随之出现的是一个手拿《新华日报》奔走呼号的报童。
抗战时期,如遇重大新闻,各个报社均有出“号外”的传统。著名画家蒋兆和曾在1936年来重庆,将路上报童卖报的场景用水墨画了出来。如今,这幅《卖报童》真迹还保存在泸州市蒋兆和纪念馆中。
这一早已消逝的职业,也将在两江国际影视城里重现。当然,这里的报童都是由专门聘请的工作人员担当,依然会满街叫卖《新华日报》。游客可以从报童手里购买报纸,这些报纸是影视城查阅《新华日报》的资料后复制而成。
影剧:激励民众共赴国难
陪都时期的重庆,成为内迁学校的集中地,大批有志于民族复兴、抗日救亡的青年学子纷至沓来。同时,一大批著名的教育家、学者来渝执教,众多文化艺术界名流也来渝工作定居。
当时,电影业在重庆相当红火。重庆有两家电影制片厂,一家是简称“中制”的“中国电影制片厂”,另一家叫“中电”。大批演艺圈人士入渝,重庆城一夜间成为了“中国电影精英避难地”,包括白杨、赵丹等一大批影星、名导演、名编剧。
当时,重庆生产的影片很多,有《火的洗礼》、《还我故乡》、《孤城喋血》、《中华儿女》、《克复台儿庄》等一大批激励人民抗战救国的电影。那时城里有名的影院不少:国泰、唯一、抗建堂、实验、劳动……影片在重庆制作,在重庆上映,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“大后方电影”时代。
影视城内复建了民国时期风格的国泰戏院,并将不定期上映当年的老电影,游客可随时购票进入,在影院内时空穿越,感受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,万众一心抗日救亡的精神氛围。
老字号:原汁原味展现民俗文化
为原汁原味展现老重庆韵味,还原更多陪都时期重庆的民俗风貌,两江国际影视城从细节入手,与百余家重庆老字号品牌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,力图将老重庆民俗更多更全、更原汁原味地展现。
他们引进了如糖关刀、炒米糖开水、糖画、蜀绣、夏布等民间手工艺和经典非遗项目,可让游客在极具时代风情的场景中“穿越”时光记忆。
街上四处可见穿着民国服装的人,很可能就是一名演员,也可能是游客。团队游客能享受专门定制剧本,以陪都时期为背景,植入各种体验感很强的故事情节,沉浸式地体验民国风情。(记者 杨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