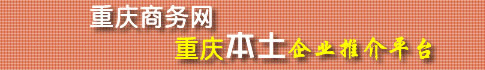十多个成年人才能合抱住树干。

经过改建的古炮楼。

陈梦华(左)经常去刘家祠堂串门。

这株老黄葛树长在围墙上,墙、拱门都被树根挤变了形。 重庆晨报见习记者 雷键 摄
重庆晨报记者 蒋艳 实习生 王思洋 报道
一座历经500余年的古代汉寨,老屋、古树、碉楼……从兴盛到没落,浓缩着一段岁月。位于重庆忠县花桥镇的东岩古寨,是汉族寨文化保留比较完整的寨院,也是中国传统村落。但这座古汉寨,如今已满是沧桑,寨里青壮年都已经离开,或外出求学工作,或外出打工,留守的只有10多个七八十岁的老人,盼着年轻人多回寨里看看。
寨门前的一株千年黄葛树,似一位老者看护着这座古寨、这片土地。
古寨 靠山面水的“风水宝地”
从沪蓉高速新立或永丰出口下道,走十几公里的乡镇公路,经过拔山镇就到了花桥镇。镇不大,最热闹的就是一条窄窄的小街。
花桥,名字很浪漫。听当地人说,最早这里有两块巨石,自然拼合成了一座桥,春天一到,石桥周围开满野花,村民就把这里叫做“花桥”。后来,因为修场镇的这条小街,花桥消失了,但名字保存了下来。
通过场镇再往前走,就是通往东岩古寨的小路。看见高高的钟楼,寨子就到了。高高低低的石垛把寨子围合起来,石头上爬满了青苔。
“这座寨子所处的地形,酷似展翅翱翔的雄鹰。”花桥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刘志荣指着周围说,这里靠山(九华山)面水(双河),“也是村里一块地势较高的坡地,是建寨人当年选中的‘风水宝地’。”
古寨里有寨墙、楼亭、栈道及明清建筑。据初考,这个村落大约有500余年历史,汉族寨文化保留比较完整。东岩古寨真正建寨并形成规模,是在清朝嘉庆年间,是刘木清前辈为了防匪修建,寨内占地近30亩,寨外占地50余亩。
以前为了防匪,古寨前面是一座长约50米、高3米的寨墙,环绕古寨前部,另三面是悬崖峭壁,使城堡固若金汤。
老树 十余个成年人才能合围树干
在拱形的石寨门上,有一株巨大的黄葛树,盘根错节,将原本细密规则的寨门拱得凸凹不平、裂缝丛生,彰显着强大的生命力。“谁也说不清楚这棵树究竟多大年纪,据初步考证约有千余年。”刘志荣说,这也是寨里最古老、最神奇的景观。
这棵黄葛树的树冠约有70米,树干也十分粗壮。在现场试了试,十余个成年人伸出双臂,才能将树干围合起来。
78岁的村民陈梦华老人,在东岩古寨住了半个多世纪。上世纪50年代,他刚搬进寨子时,这株黄葛树看上去就有这么大。
陈梦华说,上世纪80年代时,有一天突然听见“轰”的声响。大家跑出来一看,结果是黄葛古树有一根枝杈太重,掉了下来。树下有头牛正在吃草,都以为牛肯定被砸死了。结果牛被树枝“扫”进了旁边的坑洞,也没有受伤。村民更觉得稀奇,认为古树保佑着这里的寨民。“当时社员分柴火就分了好多。”陈梦华回忆,掉下来的这根树杈总共有万余斤,当时古寨里有100多名社员,每个人分了几十斤。
如今,逢年过节,或是外出返乡的人,还会在低矮的树杈上挂红布条驱灾祈福,这里也成了人们心里最深的故乡记忆。
现在,已经有黄莲等10余种树,长在这株黄葛古树里,根枝缠绕,相依相偎。
旅游 打造成乡村休闲旅游地
寨里其他建筑和装饰,并不像刘家祠堂等建筑一样幸运,很多已经在历史中消失。
陈梦华老人指着寨墙,双手用力地比划着,努力地想告诉我们当年的模样。“为了防‘棒老二’(方言指强盗、土匪),以前石墙上还有八尺高的木桩,每根木桩比腿还粗。”陈梦华说,这些木桩依次排开,足足围了寨子一大圈,看起来很神秘、很威严。刚搬来时这些木桩还在,后来就被村民拆了当柴火。
密林中的太平池,曾经碧波荡漾,有一座写着“太平池”的拱桥。后来填池造房、种竹子,池面只剩下很小一块。
东岩村村支书郭万祥说,东岩村有3000多村民,但古寨只剩下了十来户,留守的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,“鼎盛期,仅寨子里就有五六百人,寨内还有武装力量,屋子的外墙上还挂着枪。”
刘志荣介绍,2006年,曾有公司入驻东岩古寨,准备打造成旅游景点,两年后因资金不足而搁浅。在刘家祠堂的墙角,还摆着当年的规划图纸、效果图,已经蒙上厚厚的灰。
“重庆忠县计划把东岩古寨继续打造成为生态观光、文化娱乐、餐饮度假为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地。寨子发展起来,吸引人们返乡,留守的老人也不会感觉冷清了。”刘志荣说。
祠堂 保存完好,已有上百年历史
古寨里都是青石板路,数十栋明清风格的民居高低错落,民居不是常见的川东四合院,而是三合院,敞开一面迎风透阳。
走过寨门就能看到宽大的刘家祠堂,这里也是古寨保存得最完好的建筑。老屋的主梁上,用毛笔写着“大清同治六年”,距今已百多年。祠堂外墙有精美石雕,侧面的石窗上也有不同的雕刻,有的像官帽、有的似凤冠。门口高高的门槛已经踏破,能想像当年的人丁兴旺。
为何会有官帽、凤冠这样的雕刻?原来,除了建寨的大户人家刘家,一方为官的余家当年也曾在寨内居住。
年近八旬的鲁朝芳婆婆看到有人登门,连忙端出长条凳。鲁婆婆住的老屋也已经上百年,是寨里的最高点,寨门、古树、远山都尽收眼底。旁边就是以前刘家小姐的阁楼,圆形的阁门、朱红的木墙,是寨里的一抹亮色。老屋窗棂的雕花、木柱的镂纹、石礅的雕刻,无不显出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和雕刻者的精湛手艺。
但历经岁月,木窗破朽、石墙风化,宽敞的院子堆满了干枯的谷草。鲁朝芳婆婆和老伴相依为命,每顿还会喝点小酒,在寨子里过着平静如水的日子,“现在寨子里面冷清,还是希望离开寨子的年轻人,多回老家来看看。”
纵深>
重庆忠县花桥有两位历史名人
刘志荣介绍,花桥也出过很多名人,最有名的两个人,是著名实业家沈芷人(也有资料称沈芷仁)和著名烈士余永藻。
出生于1900年的沈芷人曾留学法兰西和比利时,1927年回国,在重庆与蓝义宣合资开办了隆昌义大煤矿,接着又独资开办重庆兴国实业公司。下设炼油、机制砖瓦、造纸、机器、煤矿等七个企业。1941年创办了忠州大道中学(即现在的重庆忠县拔山中学)。1948年侨居马来西亚沙巴州,大办实业,被誉为“开发沙巴州的巨人”。
烈士余永藻也是花桥人。1923年加入中国******,历任北京九区区委委员、共青团北京市委负责人。1927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,11月11日,余永藻与王荷波等18位北京市党团组织重要负责人殉难。1949年12月,周恩来****亲临主祭,将十八烈士忠骨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清代“家训”世世相传
41岁的陈永朴是重庆忠县花桥镇社保所所长,他带着记者来到二爷陈世纪家,老人珍藏着一份清代的祖宗遗嘱,也是重庆忠县花桥、拔山一带陈氏族人代代相传的“家训”。
陈永朴说,常常听老一辈讲,家族是明末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迁徙而来。最先落户重庆梁平,当年共有三兄弟,有一支又迁徙到了重庆忠县花桥、拔山一带,繁衍生息。这张遗嘱是祖辈陈信堂在年近九旬时立的,将家产分给两个儿子,而最重要的是留下了“家训”,“但愿二子勤俭立身、诗书裕后,自然子孙发达,世代重庆荣昌。”
“勤俭立身、诗书裕后,也就是说让子孙勤俭节约,也鼓励读书长学问,家族就会发达昌盛。”陈永朴说,这8个字的“家训”,代代相传,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。
陈永朴说,自己每年都会去几趟古寨,虽然现在年轻人都离开了,但只要寨子还在,感觉根就在,也能唤起家乡人的“乡愁”。
声音>
古村古寨不能被历史遗忘
“很喜欢这样的报道,寻访就是为了记住。”一位姓周的读者打来电话说,这些古村古寨的保护,应该越来越受到重视,不能被人们和历史遗忘。
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黄勇,曾多次寻访重庆市的历史建筑、街区,也参与了历史建筑和街区的保护。黄勇说,古村古寨是国家和地方现代化过程中,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“珍宝”,弥足珍贵。因此,古村古寨的建设发展,更应以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延续与创新为导向,而不宜完全采用经济价值的标准,才能留住和延续乡愁。